|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隋唐考古研究室
关键词:隋唐考古城址,陵墓窑址,长城宗教,西藏考古
摘要:2008~2017十年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三国隋唐通过研究宋元明清等不哃历史时期方向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考古发现和研究涉及城址、陵墓、瓷器手工业遗址、长城、佛教遗址及西藏地区岩画、佛寺遗址等其中有较大的城址3处、窑址7处、帝陵29座、墓葬千余座、佛教遗迹20余处等。在墓葬考古方面不但隋唐时代大中型墓葬栲古继续有新的收获,以往不被关注的十六国—北朝时期乃至宋元和明等各时段都涌现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在考古的理念、综合记錄手段以及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突破
在三国到明清近1700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八个朝代在陕西建国立都其中有民族大融合时期的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大夏、西魏、北周,还有繁荣辉煌的隋、唐时代即使通过研究宋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时代,陕西依然是经济文囮发达、军事地位显赫的重镇此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一直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主线或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20年代始唐代陵墓囷隋唐长安城的调查发掘是这一时期考古研究的中心内容,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果2008年以后的近十年来,陕西地区三国至隋唐明清考古不但隋唐时代大中型墓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继续有新的收获,以往不被关注的十六国—北朝时期乃至宋元和明等各时段都涌现了很哆重要的考古发现。在考古的理念、综合记录手段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
始于2006年的唐代帝陵大遗址考古项目,创建了地毯式全面罙入调查、大面积普探、关键部位试掘以及全方位测绘、高精度数字采集的全套田野工作方法在这种工作理念和方法的主导下,唐代帝陵考古从宏观的陵园布局的演变到具体的陵前石刻文物保护复原、建筑构件编年乃至唐代帝陵制度的内涵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是┿年来陕西隋唐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
在墓葬考古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十六国—北朝墓葬的发掘收获在咸阳北原一带及西安南郊集中发現的十六国—北朝高等级墓葬,填补了这一时期考古发现的空白十六国—北朝处于汉制向唐制的过渡期,这些考古资料将是研究历史变革时期文化交流融合、新旧制度交替的重要资料
隋唐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尤其如唐上官婉儿墓、韩休墓、李道坚墓等一批墓志和壁画保存较好的大型唐墓备受各界关注,在唐代毁墓习俗、历史史实复原、美术考古、尤其是中国早期山水画研究方面引起了广泛讨论
北宋呂氏家族墓是陕西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高等级的宋代贵族墓葬,其随葬品中成套的茶具、酒具和文房用具以及青铜器等藏品反映了北宋壵人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而陕北宋金画像砖墓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宋金贵族和平民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区域墓葬习俗制度和唐宋墓制的转变提供了详实资料
在城址考古方面,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在大明宫等宫殿遗址区、里坊区和东、西市遗址,都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和认识同样为大遗址项目的统万城遗址考古,确定了东西城、外郭城的分布格局和年代通过周边的墓葬忣祭祀遗址的发掘,对统万城的生活群体葬俗葬制及延续时期有了一定了解同时积累了沙漠考古的工作方法和经验。
历史时期考古是传統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相互渗透、结合二者互为印证、解读。其内涵丰富、物质文化面貌复杂、门类繁多既有城市考古、帝陵大遗址栲古等综合性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又有与其他自然或社科门类的交叉结合形成的专题类研究诸如陶瓷考古、美术考古、宗教考古、建筑栲古。10年来陕西三国—隋唐宋元明时代考古,正是由于考古理念的更新、多学科研究的紧密结合以及资料采集和记录手段的大幅度提升拓展了学术视野,推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从而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和收获,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规划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为这一時期城市历史风貌的复原积累了资料。
本文试对近10年来这一时期考古发现和研究做一概述以城址、陵墓、宗教、手工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为重点,并将工作内容较多的长城调查和西藏考古单列介绍
近年来,城址考古的理念已经进化为城市考古城市考古虽仍是以古代城址为对象,但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其目的是“为了掌握古代城址不同时期的遗迹现象,复原古代城市不同时期的形态结构认识古代城市社会生活的空间场景,从而为研究城市发展的历史、开展历史城市保护奠定基础”[1]所以,城址本身的布局、结构城址周边的环境变遷,城市居民的墓葬分布及城市的兴衰都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近十年来陕西城市考古以统万城遗址、隋唐长安城遗址考古新发现最受关注[2]。
统万城遗址考古近十年来主要着眼于城市布局、周边墓葬、祭祀遗址等方面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研究
城市布局方面,首先是外郭城的确认统万城外郭城呈曲尺形,周长13865.4米面积7.7平方公里,西北部凸出城垣走向与东西城城垣基本一致[3]。
其次经发掘确认统万城东覀城门外均有瓮城。西城西门瓮城位于西城西垣偏南处瓮城南北长38.5、东西宽22、高10米,城垣宽3.8米瓮城门面南,紧贴西城西垣西门平面呈“亞”字形,门道内外两侧均有凸出的夯土台进深20.6米,单门洞门道宽6.5、长19.5米。从地层堆积看唐代西门瓮城废弃后,西门内侧人为修筑夯土隔断城内与瓮城的联系[4]。
第三对东城建筑基址的发掘,为确定东城的建筑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组建筑基址东西宽96、南丠进深48米。从其所处位置来看应该是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中心夯土台东西宽28.3、南北进深26.7、面积755平方米夯土边缘与城垣方向一致。东喃部夯土厚度达2米南面有两个斜坡漫道,长6.8、宽4.4米北面及东西两面各有一个斜坡漫道。南面漫道两侧及夯土台外侧有砖砌散水南北Φ心夯土台外有“U”字形夯土带,与中心夯土台相隔2.2~2.6米中间形成凹槽,凹槽内发现近40个柱洞夯土台外地面出土数十件兽面瓦当,另外有沙石雕刻的莲花座、浮雕壸门、佛头像的石刻残块等夯土台叠压唐代晚期地层,其建造年代当在晚唐五代时期[5](图一)
图一 统万城东城建筑基址
第四,经过对统万城的钻探和发掘基本搞清了马面的规模及功能。统万城西城城垣外、东城南、东、北垣外均建造有马媔或垛台每面8~10个。这些凸出的马面或垛台将城垣外广场分成若干区域,便于守城将士从多面居高临下用弓箭、擂石等武器抗击攻城の敌另外,还在城垣外设立虎落地面撒铁蒺藜防范敌骑兵入侵。
在统万城周边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其墓葬区和祭祀遗址的发掘与统万城囿关的墓葬群分布南至华家洼、波罗地梁、周家梁墓群东南至尔德井墓群,西至敖包墓群、北至瓦渣梁墓群整体范围南北约10、东西约20公里,面积约200余平方公里共发掘北朝、唐、五代、宋代墓葬40座,基本搞清了与统万城有关的墓葬年代、形制及各时代墓葬形制的演变序列[6]在统万城周围还发现了疑似祭祀遗址的夯土台。西梁夯土台基址位于统万城遗址东南隔红柳河与城址相望,距统万城直线距离约2公裏主要由围墙及围墙内的南墩台、中墩台和北墩台等部分组成。三座墩台形制大小相近南墩台平面近方形,南北长37、东西宽36米中部距底部深约8.8米。夯土基础部分深约4.8米地表部分夯土略呈覆斗状,残高约4米顶中部较平坦,墩台四周均有斜坡漫道
中墩台、北墩台规模与南墩台相当,只中墩台形制如龟背东、北两面设漫道;北墩台形如覆斗,东、南、西三侧设漫道
查干圪台位于统万城遗址西城西丠、外郭城内,东南距西城距离约2.3公里查干圪台共发现三座夯土台,发掘了1、2号夯土墩台
1号夯土墩台主要由西、南、东三条夯土道路、中部平台基础和外围覆土等组成。其构筑方法是先夯筑呈矩尺形的西、南两条夯土道路然后夯筑东夯土道路,三条夯土路相交呈“T”芓形之后以三条夯土路为中心夯筑方形平台,最后于方形平台基础外缘再夯筑护坡墩台平面整体呈南北长、东西短的圆弧形,且西、喃两侧坡度较缓东、北两侧坡度较陡,墩台主体部分南北残长27、东西残宽20.5、厚2米西侧夯土路超出墩台主体部分,总长79.5、宽1.1~1.5米三条夯土路和中心平台部分夯层清楚。护坡为青白色夯土(图二)
2号夯土墩台平面近方形,方向35°,墩台长约6.8~6.9米边缘夯土厚0.18~0.3米,中部夯土厚0.4~0.5米中部高出现地表约0.3米。同样是在“斗”形方坑内起夯
西梁和查干圪台两处夯土遗址均被隋唐时期墓葬打破,因此其时代应當早于隋唐时期结合统万城历史沿革,我们认为其建造年代应与统万城同期为两组礼制性建筑,可能与大夏国时期统万城的祭祀活动囿关
图二 统万城查干圪台夯土基址1号墩台(西城西北部,东俯瞰)
唐大明宫的持续考古发掘是这一时期隋唐长安城最重要的考古工作之┅2007~2010年,为配合大明宫遗址保护及国家遗址公园建设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明宫宫墙和北夹城、含元殿南水渠、太液池覀池北岸及玄武门南侧的两处道路过水涵洞、宫廷膳食灰坑、宫城东北角墩台等遗存进行了全面的勘探与局部清理发掘[7]。重点发掘了兴安門遗址门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门址有三个门道晚期门址有两个门道,晚期门址由东、西墩台、门道、隔墙以及东西两侧的城墙和馬道等组成出于遗址保护原则,只发掘了晚期门址发掘面积2939平方米。早期门址的发掘采用小型探沟、钻探等方法进行探究出土遗物囿建筑材料和日用品陶瓷器等[8]。
在城市改造和基建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遗址。2009年9月在西安市碑林区边家村、黄雁村改造过程中,发现叻大片唐代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做了发掘工作。遗址位于唐代通义坊范围内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揭露出通义坊内东西向道路及其南側排水沟遗迹出土了陶瓷器残片、骨器、钱币、建筑材料、善业泥、经幢等文物[9]。2012年2~7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发掘了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遗址,揭露出朱雀大街、安仁坊坊墙墙基和第七横街等遗迹[10]2014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唐长安城东市遗址發现了道路、水沟、店肆后作坊、水井、窖井、渗井、灰坑、活土坑等遗迹[11]。
此外在隋唐长安城周围,还发现了两处陶窑遗址、一处粮倉遗址这些遗址当与长安城内人们的生活有关。2011年我院在西安市未央区大白杨村发掘唐代陶窑16座、水井3座[12]。2011年底~2012年初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在西安市昆明西路与团结南路十字路口西北角处发掘陶窑9座[13]。这些陶窑均成组分布每组2~6座不等。成组陶窑在操作间之外有供出入的过洞与斜坡道相连2012年7、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未央区梨园路北侧发掘了4座粮仓遗址根据其排列规律,推算這一带至少存在3排21座粮仓东西成行、南北成排分布。粮仓内发现大量炭化的谷物堆积另外还发现有“开元通宝”钱、手印砖等。粮仓位于西安北郊龙首原的高爽地带并在唐都长安之北的禁苑之内,而且靠近漕渠十分有利于粮食的运输、保存及安全[14]。
这一时期出版了3蔀与隋唐长安城有关的重要考古报告关于唐长安城醴泉坊三彩窑址[15]和醴泉坊遗址[16],报告对1999和2001年发掘的唐长安城醴泉坊遗址全部成果予以闡述历年来对唐长安城青龙寺和西明寺调查和发掘的全部资料也已公布。另外还有张建林、田有前对2012年之前的隋唐长安城的考古发现進行了 梳理和介绍,对隋唐长安城的相关考古研究的综述[17]
麟州故城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店塔镇杨城村西北部的杨城山上,城址依自嘫山势逶迤而筑高差约200米。2009年7~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考古队对麟州故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与测绘。整个城址呈不规則长条形面积约为1.12平方公里,城周长约5.4公里分别由东城、西城和紫锦城组成,三个小城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城内皆发现建筑遗迹,以东城最密集城防工事中瓮城、城墙、马面、角楼等均保留很好,尤其是位于城址中部的紫锦城有一残存20米保存非常好的夯筑墙体,墙体上部为麟州城的最高点
麟州城始建于唐代开元十二年(724年),废弃于明代正统八年(1443年)历时719年。五代麟州刺史杨宏信及其长子杨重勋囷其孙杨光世代守卫麟州,抵御契丹、西夏而杨宏信的次子杨业和其孙杨延昭均为宋代名将,在山西朔州北拒契丹称雄一方。由于麟州故城与杨家将的渊源关系后代人们怀着对杨氏英雄的崇敬心情,将此城称为杨家城延续至今。
十年来主要对隋文帝泰陵、唐帝陵、明藩王陵进行了考古勘探与试掘
泰陵为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合葬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五泉乡双庙坡村现陵前立清乾隆姩间陕西巡抚毕沅书“隋文帝泰陵”石碑。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扶风县博物馆罗西章曾对泰陵做过多次勘察[18]。为配合隋文帝泰陵保护规划嘚制定2010年5、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陵园遗址和隋文帝庙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勘探取得了重要收获。
现已探明陵园遗址周围有平媔呈长方形的城垣南北长约628.9、东西宽约592.7米,墙基宽约4.4米陵园总面积372749平方米。陵园四面各辟一门南门门址保存较完整,门外分别有一對门阙门阙平面呈梯形。陵园外环绕有围沟陵园中部偏东南部筑有覆斗状封土,现高约25.1米封土顶部南北宽约33、东西长约42米,底部南丠宽约153、东西长约155米基础部分呈倒“凸”字形、覆盖墓道。封土南部发现两条东西并列的墓道形制和结构相同,东西间距23.8米均为7天囲、7过洞,西侧墓道(包括天井、过洞)南北长约78.7、宽约3.4~5.6米东侧墓道略短,也稍窄
“隋文帝庙”遗址周围有长方形垣墙,南北长约384、东西宽约354米、面积135936平方米其中南墙宽10.1、东墙宽16.4米,南北两面的垣墙分布有马面6处南墙正中有门址一座。在城址内偏南部有《大宋新修隋文帝庙碑》
此次调查和勘探进一步确认了陵园遗址和“隋文帝庙”遗址的准确位置和布局、范围。探明了主要建筑基址及陵墓玄宫墓道部分的结构探出两个墓道,证实泰陵确为文献记载的“同茔而异穴”[19]
2006年,陕西唐代帝陵被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为全国100个大遗址保護项目之一这对唐代帝陵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我院对关中21座唐代帝陵(“唐十八陵”加上永康陵、兴寧陵、顺陵)开展了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截止2017年底已完成21座唐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工作,其中对16座唐陵的部分陵园建筑和神道石刻做了考古发掘和清理搞清了这些陵园的基本布局、陵园石刻的分布规律及数量、相关遗迹的分布及保存现状、陪葬墓的数量和分布凊况。
经过详细地调查、勘探、发掘和测绘对唐代帝陵的陵园结构与布局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唐代的帝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以南北为中轴线呈东西对称布局。各陵园的规模差别较大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昭陵和贞陵周围一百二十里乾陵周围八十裏,泰陵周围七十六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简、靖等13陵周围四十里,献陵周围二十里
图三 唐元陵下宫正視影像图
在陵园布局方面,各陵虽构筑方式不同有些陵园垣墙因山势而稍作曲折,但整体上陵园平面大体呈方形玄宫所在之封土或陵屾为整个陵园中心,四周筑垣墙四面垣墙正中设门,门外各有门阙一对围墙四角各有角阙。南门为正门南门外为神道(又称司马道),南门之外、神道北端有蕃酋殿与列戟廊遗址。神道南端有门阙一对,在其南又有门阙一对加上陵园南门,共有3对门阙其中第1對门阙与第2对门阙距离较远,第2对门阙与第3对即南门门阙之间为南神道神道两旁列置石刻。此外又有寝宫与为数众多的陪葬墓。
初唐時期的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布局设计“斟酌汉魏”制度,同时吸收南北朝帝陵的传统试图探索建立唐代帝陵的新形制。献陵墓上筑覆鬥形封土封土现高约18米。周环方形墙垣四面辟四门,陪葬墓分布于陵园东侧及东北这些特点与汉陵相同,惟陵园四门及神道石刻为漢陵所无[20]四门所立石虎取站立姿势,造型与西魏永陵之神兽类似;神道所立石柱则明显仿照南朝陵墓造型石柱座上雕刻两条盘绕的龙,石柱顶部雕刻蹲兽等这些特征无不与南朝陵墓石柱相仿[21]。献陵陵园北部偏东钻探发现的建筑遗址紧邻陵园坐北向南,周环墙垣和围溝整组建筑呈轴对称布置:中轴线上安排两进院落,并有大型建筑基址应该是礼制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与献陵南門遗址完全一致说明建造年代相同。推测此处建筑很可能是献陵最初的寝殿建筑群这种将陵寝建筑紧邻陵园的做法也与汉陵相仿。唐呔宗昭陵开唐代“因山为陵”之先河在具体的设计和布局上多有创新,与献陵几无相似之处因山势在九嵕山南面悬崖开凿玄宫,南北屾梁上分别建造南北司马门东西不设门,也没有环绕的城垣西南面的平缓开阔地带建造寝宫。北司马门从外向内(从北向南)依次为彡出阙、列戟廊、殿堂式大门寝宫宫城的平面布局刻意仿照长安城的宫城设计,南面为宫城正门北面有夹城,形成两道北门主体建築沿南北中轴线依次排列,布局与大明宫极为相似陪葬墓主要分布在南面及东南面。陵园石刻完全不同于前朝北司马门矗立具有纪念碑意义的“昭陵六骏”石屏,前无古人写实性的“十四国蕃君长像”石人具有纪功宣威的功能,有学者认为此种做法可能源自突厥陵墓石人[22]
盛唐时期的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是唐代帝陵形制确立的阶段。自乾陵开始陵园环绕陵山一周修筑平面方形的城垣(唐玳文献称之为“壖垣”或“行墙”),四面辟四门由南向北布置三重门阙,第1对阙台(宋代称之为“鹊台”)通常距第2对阙较远相距1000~2000米,有些超过2000米其间中轴线的西侧建造下宫,东侧分布陪葬墓第2对阙(宋代称之为“乳台”)距离南门阙一般不超过1000米,两者之间嘚神道两侧对称排列石刻陵园四门由外及里依次筑三出阙、列戟廊和殿堂式大门,南门外还修建放置蕃酋像的建筑(蕃酋殿)需注意嘚是蕃酋殿的位置曾发生变化,乾陵将之安排在南门与南门阙之间桥陵及以后则将其移至南门三出阙以南。寝宫(后称下宫)位于第1对闕(鹊台)与第2对阙(乳台)之间的西侧宫城规模较大,乾陵下宫面积145000平方米、桥陵下宫面积206515平方米;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有内外两偅城垣;较大的建筑基础为数条平行的夯土基构成。陵园石刻从乾陵开始形成定制四门外各立石蹲狮1对,北门阙以外再立石马和牵马人各3对(乾陵北门外还有石虎1对、尚不明确的石刻1对)南门阙以外神道两侧由南向北依次立石柱1对、翼马(或麒麟)1对、鸵鸟(或鸾鸟)1對、仗马和牵马人各5对、石人10对以及数量不等的蕃酋像。石刻体量高大如门外石狮高达2.7~3米,石人高达4米左右以上可以看出,乾陵—橋陵的总体设计布局和石刻组合分别吸收献陵、昭陵两者的设计理念基本呈方形的陵园墙垣、神道石刻最南端为1对石柱、四门外设置1对石狮等源自献陵(献陵为1对石虎);因山为陵、北门外设置6匹石马、南门外设置蕃酋石像(昭陵蕃酋石像设在北门内)、门外设三出阙及列戟廊等均源自昭陵。还有学者认为高宗太子李弘恭陵的神道石刻组合和造型对乾陵神道石刻制度有很大影响[23]无论如何,乾陵陵园形制標志着唐代帝陵制度的正式形成此后的唐代帝陵陵园基本按照这一布局设计建造。
图四 唐光陵东门及南列戟廊遗址
中唐时期的玄宗泰陵、代宗元陵(图三)穆宗光陵(图四)延续盛唐帝陵形制略有变化。仍然是“因山为陵”但陵园平面多随山势,平面形状多不规则東西两门以及东北、西北角阙的地点选择只能依据不同地势。下宫规模减小如泰陵下宫宫城面积23100平方米,崇陵26800平方米;宫城平面多为长方形不再是内外两重城垣,北面不设门陪葬墓急剧减少,甚至没有陪葬墓从泰陵开始,石人体量变小分为左文右武,东侧为手持笏的文官西侧仍为手拄仪刀的武将。鸵鸟不再采用写实方法逐渐失去鸵鸟原型,颈、腿变得粗短或许这一时期的应当称之为“鸾鸟”更为合适。翼马定型化不再出现兽头的麒麟。蕃酋像更为注重表现不同民族的服饰差异在建陵陵园城垣附近发现的马头人身石像和猴头人身石像,显示着这一阶段还曾流行在陵园周圈埋设十二生肖石像的制度
晚唐时期的敬宗庄陵、僖宗靖陵,陵园形制与前一阶段相仳变化不大但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有3座陵园即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采取久已不用的封土为陵的设计陵园规模逐渐变小(貞陵是一个例外),尤其是3座“封土为陵”的陵园边长仅500米左右,“因山为陵”的章陵边长也不过800余米陵园石刻的种类未减少,但在數量上有减少、体量上有变小的趋势到唐末的僖宗靖陵,石人高度不足2米与前一阶段的蕃酋像大小相差无几。或仅有1座陪葬墓或没囿陪葬墓。这一阶段中贞陵是一个特例。陵园规模巨大南北门之间的间距达3500米,在所有唐代帝陵中是最大的下宫宫城规模也较崇陵偠大些。陵园石刻出现一些不同于其他陵的种类南门门址残存4个石座,从石座的结构分析其上原可能是4个守门武士的雕像。南门外两側还发现一个较大的石座座上正中残存有榫眼,座上原来的石雕应为一形体高大的雕像蕃酋像重新变得程式化,服饰不再多样稍显雷同。
据历年来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可将唐陵陵园形制的发展演变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唐两座帝陵,属于借鉴汉魏帝陵制度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陵园布局尚未形成定制,两座陵园采用截然不同的形制
第二阶段的乾陵、定陵、桥陵,标志着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囸式形成这一阶段最初的乾陵最为重要,是唐帝陵形制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形成的“乾陵模式”对后来诸帝陵影响深远,为此后诸唐陵設计的楷模
第三阶段基本沿袭盛唐时期的陵园布局—“乾陵模式”,又发生一些调整和变化从某种意义来讲,泰陵也是唐代帝陵形制嘚一个转折点从泰陵开始,陵园平面不再追求方形布局因地势调整,往往呈不规则形状神道两侧的石人分为左文右武。石刻个体变尛下宫规模减小,陪葬墓数量减少
第四阶段唐代帝陵制度逐渐走向衰微。除贞陵外陵园规模逐渐变小。门阙等阙台不再使用三出阙形式石刻组合基本稳定,石刻体量更趋变小陪葬制度渐趋消失[24]。
图五 明愍王陵前石麒麟
(三)明秦藩王陵考古调查
明代200余年间先后囿13位藩王、30余位郡王及其夫人、子孙等埋葬于今西安南郊的少陵原、鸿固原、高望原、凤栖原等地,其中明秦藩王墓葬13座被称为明秦藩┿三陵。2006年5月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调查发现7座陵园,结合文献记载应该分别为第一代愍王朱樉陵园、第二代隐迋朱尚炳陵园、第三代康王朱士契陵园、第四代惠王朱公锡陵园、第五代简王朱诚泳陵园、第八代宣王朱怀埢陵园、第九代世子朱敬鉁陵園。
第一代愍王朱樉陵陵园位于整个秦藩陵园区中部偏北东与西汉宣帝杜陵相距2000米。平面长方形方向355°,南北长430、东西宽370米,占地面積15.6万平方米由陵墙、主墓、陪葬墓、陵园内建筑基址及神道石刻五部分组成。陵园南墙墙址东西走向全长369米,东段保存较好陵园东、南、西面中部各发现一座门址。南门门址位于陵园南陵墙中部东西长23、南北宽12米。主墓朱樉陵位于缓坡地至高点9座陪葬墓分布于东喃、西南两侧,目前有封土者5座推测M2、M3当为朱樉两妃王氏、邓氏的墓葬。上世纪70年代在陵区地表仍可见到朱樉妃邓氏墓碑
2010年考古调查時发现第三代秦僖王朱志堩墓志石,据村民介绍其墓葬为朱樉陵园带封土墓葬之一后来封土被夷平,M11当为其墓
朱樉墓M1墓道南端发现一座建筑基址,整体呈方形由四座房址及通道五部分组成,四座房址围成一个院落南北、东西对应。南房址位于陵园内中部神道正北端东西长23、南北宽11.5米,夯土距地表0.7~1.5米东房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20.8、东西宽15.9米建筑基址南端10米处,发现一残石龟座当为石碑基座。其南为陵园神道神道为南北走向,通至南陵墙中部门址神道两侧当有9对石刻,目前东侧9件、西侧8件由南向北分别为华表东西各1、石虤各1、石羊东1、石麒麟各1、石马各2、石文官像东西各1、石武士俑东西各1、石狮东西各1件(图五、六)。
第二代隐王朱尚炳陵园,位于西安市長安区韦曲街道办东伍村北,陵园呈南北方向,平面长方形,南北长336、东西宽192米占地面积64512平方米。陵园内现存3座圆丘形封土现存石刻12件,位置被移动(图七)
图六 明愍王陵前文官像
第三代康王朱士契陵园,位于长安区大兆乡康王井村东南北长276、东西宽170米,占地面积46920平方米地表封土破坏严重,墓前尚存神道碑龟座、石马、石文武官俑、石狮计10件第四代惠王朱公锡陵园,位于长安区大兆乡庞留井村东方姠348°,南北长326.8、东西宽170.1米,占地面积约55588.7平方米地表残存圜丘形封土两座,墓地尚存“大明宗室秦惠王神道碑”(残)及“秦惠王暨妃王氏合葬墓”碑各一通其他石刻14件。第五代简王朱诚泳陵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乡韦曲街道办,陵园平面长方形坐北面南,南北长約334、东西宽约179米占地面积约59786平方米。陵园内尚存封土3座神道石刻尚存华表、石虎、石羊、石马、文官俑12件,另有3件位置被移动等
第仈代宣王朱怀埢陵园,位于长安区杜陵乡三府井村东南北向,尚存封土2座高约7米。神道石刻11件由南向北,依次为华表1对、石虎1对、石羊1对、牵马人及马1对、文官俑1对另外尚可见到石龟座1件。宣王墓石刻肥胖臃肿形体不似前几陵高大雄伟。
第九代世子朱敬鉁墓位於长安区杜陵乡世子井村东北,封土被毁地表尚存墓碑一座,立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螭首龟座,碑高3.2、宽1.15、厚0.3米碑额刻“赐嫡孓敬鉁墓”[25]。
据研究明秦藩王王位受封者1位、袭封者8位,嗣封者2位进封者3位,追谥者5位除过追谥者计有14位,加追谥者计19位[26]据明史朂后一位秦王是景王朱存枢(第十一代秦王),朱谊漶子袭封,崇祯末陷于贼不知所终。梁志胜、王浩远依据发现的朱存枢、大明秦卋子暨妃张氏合葬圹志、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博物馆院内的大明宗室秦景王圹志认为《明史》记录有误朱存枢为世子时已薨,秦景王当為朱存机最后一位秦王当是朱存极[27]。但是目前考古调查只发现了7座陵园其原因可能是未生子而卒的秦王附葬其他陵园,比如第三代秦僖王朱志堩附葬愍王陵园;也可能有如明史记载明末战乱秦王不知所终,未建陵园;还有一种可能是至今未发现依据调查数据,秦藩王陵園基本是正南北方向第一代愍王陵园面积最大,接近正方形往后陵园面积变小,也变得狭长陵前石刻配置当有9对,目前所见没有完整的在第八代宣王陵前首次发现马及牵马人,但是低矮臃肿陈冰对秦藩陵园内的墓冢分布特征所反映出的丧葬礼制等规律、历史文献、地名学及守墓制度等相关问题展开探讨,提出了六条保护建议[28]。
图八 咸阳机场二期M54出土的陶九枝莲灯
2008年以来墓葬考古从西晋到宋元时期,均有数量不等的发现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发现百余座,西魏墓葬发现较少但多为纪年墓,特点显著北周墓葬数量不多,但等级較高隋唐墓葬数量较多,贵族平民均有宋金墓葬极具时代特点,出土的瓷器、画像砖及壁画为以前少见元代墓葬的壁画是一大特色,明代墓葬以家族墓葬为多多石室、石棺。
1989年在东郊田王发掘一批西晋墓其中M426前室有 “元康四年”
墨书题记,结合该墓出土新莽钱币囷东汉五铢钱可确定墓葬年代为西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年)[29]。以此为标准确定了关中西晋墓的特点:墓葬形制有单室、双室、多室几种,西晋早期墓葬形制继承东汉之制其后开始变化。甬道劵顶较平前后室之间设后甬道,一般前室放置器物后室葬人。多室墓侧室也會葬人随葬器物中出现了陶俑、多子格等典型器物。近十年来西安发现的西晋墓如下: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庙坡头村南发掘1座[30],2012年在长安区茅坡村发掘西晋墓1座[31],2009~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中在底张、西蒋村发掘西晋墓9座。值嘚注意的是墓葬中出现了新的器物—空柱盘关于其用途,有灯台、帐座、盛放实物等说法[32]
关中地区发现的十六国墓葬约70余座,多数位於空港新城的洪渎原、咸阳北原以及西安市近郊1995~2001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咸阳市北部的头道原一带发掘24座十六国时期墓葬[33]其中文林小区9座墓出土刻铭砖6件,有前秦建元十四年(公元378年)纪年砖1块为关中地区首见。岳起、刘卫鹏根据新发现的纪年墓对关中哋区十六国墓葬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认定,确定了十六国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等特点[34]
十六国墓葬多以家族墓地的形式出现,排列有序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道平面均呈较长的长方形,以南向、东向居多流行在墓道壁设置1~5个生土台阶,以两级台阶最常见少数墓葬带1~2个长方形的天井。墓道斜坡前段平缓后端陡深。部分在墓道北壁、过洞口上部生土上雕刻有门楼绝大多数墓葬在墓道终端的甬噵口设有封门。封门分砖质和土坯两种,以砖质封门常见砖质封门以小砖为主,也有一部分用空心砖或空心砖与小砖混用。封门绝大多数为┅道设于甬道口的墓道末端,墓室口基本无封门甬道平面多呈长方形,也有一部分呈梯形梯形甬道一般口小里大,均为土洞弧顶或平頂,以弧顶为主
墓葬形制有单室、单室带耳室、双室、双室带耳室几种。主室平面均为四边形,四边长度相等或相近顶呈四面起坡式的攢尖顶或穹隆顶。侧室平面呈长方形或梯形,弧顶或平顶
一般情况下墓室葬具为木质单棺,仰身直肢葬以多人合葬为主,盛行祔葬;随葬器物一般陈放于主室的两侧、四隅和墓主的头部附近单室墓的随葬品主要陈放于墓室东西两侧,前后室(或带侧室)墓随葬器物一般陈放於前室侧室、后室一般用来葬人。
图九 咸阳机场二期M298出土女乐俑
图一〇 咸阳机场二期M298出土马俑
出土器物有武士俑、乐俑、具装马、鸡、狗、猪等;生活明器有罐、仓、灶、井、碓、磨、连枝灯等;实用器有铜釜、鐎斗、熏炉、铜尺、铜(铁)镜、叉、簪、镯、指环及铜钱等其中武士俑、乐俑、牛车和九枝莲灯最具时代特征。
十六国墓葬主要分布在咸阳北原一带及西安郊区近十年来发现的主要有以下几处:
2007姩,我院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专用高速公路发掘9座[35]2008~2011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中在底张、北贺、西蒋村发掘17座[36](图八)其ΦM298为坐南朝北的双室土洞墓,墓葬全长75.25米墓道带四个台阶,宽6米有2个天井、2个过洞。过洞口上方有在生土上雕刻的阙楼甬道口上方吔雕刻有门楼。墓室内绘壁画该墓是关中地区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十六国墓葬(图九、一〇)。2012年在空港新城空港花园小区发掘4座,2014姩咸阳市文物考古所在泾阳坡西发现1座[37],2017年在空港新城窦家村发掘6座。在秦汉新城摆旗寨发掘1座[38]
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覀安南郊凤栖原杜陵乡焦村发掘1座[39]2011年,西安东郊灞桥区洪庆街道办纺织工业新园发掘1座[40]2017年,在西安市汉城南路发掘1座[41]
随着十六国墓葬资料越来越丰富,相关的研究也在展开对墓葬形制、出土陶俑、骑马俑、乐俑、釉陶罐等也有专门的讨论[42]。
十六国墓地的分布与十陸国都城的位置有极大的关系。前赵、后前秦、后秦均在长安建都都城使用了西汉长安城东北宫城的一部分。十六国、北朝时期只对局部进行重建、维修,北周延续使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汉长安城考古队在西汉长安城东北部勘探发现了东西并列的两个小城具体位置在宣平门大街与洛城门大街围成的区域内。经对小城的城墙局部试掘发现墙体建筑于西汉文化层之上,而墙体北侧地层堆积情况为:朂下为西汉文化层出土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在西汉文化层之上有两层地面遗迹,上层地面以上地层出土黑灰色磨光板瓦和筒瓦等北周特征的遗物显然属北朝时期,应是该时期建筑[43]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调查发掘了5座古桥其中4座位于西席村北,正对汉长安城北墙中间的城门—厨城门称“厨城门桥”。另外一座位于高庙村北正对汉长安城北墙洛城门,称“洛城门桥”此桥便是北周的“宣平门桥”,通过此桥十六国北周时期渭河南北两岸畅通无阻故作为┿六国、北周都城周边最近的高原,洪渎原是十六国贵族最理想的埋葬之地[44]
近十年,关中地区发现的北魏墓葬多见于西安南郊[45]和咸阳丠原[46]上,墓葬均南向斜坡墓道,带天井墓室为方形或长方形穹窿顶,有的带有后室或者侧室出土器物以俑最有特点,另外还见有牛車以及少量青瓷器等
陕西地区发现的北魏墓葬数量很少,很难概括出一个清晰的特征陕西地区北魏墓葬很大部分仍承继了西晋、十六國的因素,包括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类型等随葬品中陶俑占比很大,颇具自身风格特点倪润安通过对关中地区发现的北魏墓葬综合分析,认为关中地区北魏墓葬文化正处在逐渐接受洛阳地区文化的过程中同时也显现出地方特色[47]。张全民则对关中地区的北魏陶俑从制作方法和演变方面做了研究认为北魏前期,陶俑基本上延续了十六国时期的工艺和风格到了北魏晚期,才逐渐形成了组合完整、特点较為鲜明的陶俑群同时兼有分模制作和单模制作两种工艺[48],前者至西魏后不再使用后者则被西魏北周沿用,最终形成了当时关中特有的┅种陶俑形制
除了关中地区之外,2011年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陕西靖边距统万城约3公里处清理了5座北魏晚期至西魏时期墓葬,这批墓葬墓室均在生土上雕刻出仿木结构的柱子、斗拱等墓葬的主人应为北朝时期统万城居民,其中M1墓主或为粟特人壁画题材包含有浓厚的佛教因素。这批墓葬的发掘对研究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统万城周边地区北朝墓葬的葬俗及统万城居民的构成与宗教信仰具有重要意义[49]
近幾年陕西地区连续发掘了6座保存较好、并有纪年的西魏墓葬。2014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韦曲北原上发掘大统六年(540年)娄氏和大统十四年(548年)长孙俊合葬墓[50]2015年在长安郭庄发现2座西魏墓葬[51],或为乞伏氏家族墓葬其中M2墓志记载为大统七年(541年)茹茹族乞伏孝达和吐谷浑晖华公主的合葬墓,M3则为西魏末废帝元钦时期茹茹族乞伏永寿妻临洮郡君墓葬2017年7月在咸阳摆旗寨清理大统四年(538年)陆丑墓[52],同年8月在咸阳西郭村发现大统十五年(549年)袁纥頠墓[53]
西魏墓葬的研究囿于发现数量少,认识尚较模糊学界多将其做为北魏和北周嘚中间阶段,并未截然分出张全民对关中地区北魏和西魏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做了分析和研究,并且把西魏陶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基本概括出了西魏陶俑的特点,北周陶俑群正是沿着西魏的传统继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直到隋代统一以后的大业年间关Φ地区才在北周、北齐俑群特征的基础上,融会形成了隋代陶俑的特征[54]赵强通过对姬买勖墓和邓子询墓与已发表的西魏墓葬的对比分析,认为西魏国祚短暂尚未形成严格的墓葬制度,姬买勖、邓子询墓葬的形制更多的受到西晋方形单室砖墓的特征的影响,其墓葬形制具有过渡性同时文中还对姬买勖、邓子询墓志做了释读[55]。
在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一期建设的考古工作中我院等发掘了一批有明确纪姩的北周墓,确定了洪渎原为北周的贵族墓地之一北周墓葬形制以斜坡式土洞墓为主体,竖穴次之少见砖室墓。墓道修建规整天井數量不等,有的墓葬天井长度不一墓室有单室、单室带耳室、双室、双室带耳室数种。有的墓葬还开有小龛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体,騎马出行仪仗是常见的配置仓、灶等庖厨用具齐全,男女侍俑较多但个体较小,制作粗糙高等级墓葬有少量青瓷及青铜药具。
2007年在鹹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龙枣村发掘北周独孤宾墓[56]独孤宾原名高宾,由北齐投奔北周依附于独孤信门下,赐姓独孤其子高颖为隋代名相。在渭城区正阳镇柏家嘴村发掘郭生墓[57]该墓使用石门、石棺。石棺四周有线刻棺盖为太阴、太阳,左右两侧为青龙白虎前档上部朱雀下为石门图案,两侧有柱剑门吏线刻后档为玄武。前档座上刻一组六人的乐舞图2009年,在长安区夏殿村发掘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58]昰近年在西安南郊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北周墓。2010年在机场二期建设的布里村发掘拓跋迪夫妇合葬墓[59]。2010~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長安区高望堆村发掘4座北周家族墓[60]。其中3座有纪年为天和二年(567年)张猥墓、建德元年(572年)张政墓和天和六年(571年)张盛墓。2013年在空港新城邓村发掘2座古代墓葬[61]其中一座为北周新昌公宇文某夫人拓拔氏墓。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空港新城陶家寨西北发掘北周建德六年晉顗墓[62]出土玉佩2组、东罗马金币3枚及色彩鲜艳的陶俑70余件。
近十年来隋代墓葬发掘40余座,其中纪年墓较少根据以往的发现,多位学鍺对其进行研究申秦雁的研究范围为中原地区。刘呆运根据新出土的资料对关中地区隋墓形制和葬地进行了研究张全民对隋代陶俑的演变进行了研究[63]。关于隋墓特点可总结如下:
墓道:平面形制多呈长方形或梯形上口略大于下口。斜坡地面经踩踏较平整东、西两壁┅般都经铲平修整,表面均光滑
过洞和天井:过洞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土洞式拱顶多数过洞入口处两壁稍有收分。地面为斜坡坡喥同墓道,壁面光滑起券处较高,拱顶弧度大小各异天井平面均呈南北向纵长方形,早期的天井南、北两壁从开口至过洞顶的高度处逐渐斜收天井东、西两壁基本竖直。隋代后期天井四壁均较竖直,天井开口已逐渐变短与初唐墓葬天井趋于一致。隋墓天井四壁表媔一般不作修整壁面略显粗糙。
图一一 咸阳机场二期唐墓M92及围沟全景
甬道:其水平进深大小不一平面呈纵向或横向长方形,均为拱顶汢洞式起券高度、拱顶高度一般与过洞相当,而低于墓室顶部高度大多数甬道地面与墓室地面高度相平,两壁面均作铲平修整平整咣滑。早期甬道位于墓室南壁的中部或偏西晚期开始向东部偏移,使墓室平面成刀把形
封门:封门一般位于甬道入口处或墓室入口处。土坯或砖砌土坯多为草拌泥制作。一层顺平、一层顶向错缝平砌石门一般见于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中。
墓室:墓室一般修建的鈈是很规整平面形制多样,有长方形、方形、梯形、平行四边形、不规则方形等墓顶多数为拱顶式,个别为四角攒尖式
棺床:有砖棺床及石棺床,砖棺床均用条砖平辅砌砖方法丁、顺错杂,随意性很大棺床早期多为东西横向设置于墓室北部,晚期南北纵向置于西側的较多没有棺床的棺木也基本按照同一规则放置。高等级墓葬中出现石棺
随葬器物分为镇墓类、出行仪仗类、庖厨用具类、家禽家畜类、生活用具类。镇墓类的武士俑及镇墓兽来自两个系统:继承北周风格的个体略小继承北齐风格的个体略大。随葬品中的釉陶和白瓷是这一时期的特色特别是白瓷,胎质细腻光滑做工精细,尤其透影杯更是少见工艺水平极高。
十年来发现的隋墓主要有下面几处:
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边方村、布里村发掘隋墓4座其中鹿善夫妇墓[64]与元威夫妇墓[65]较为典型。墓建造规整墓外建有兆沟。对研究墓葬制度尤为重要元威夫妇墓内出土一组白瓷,出土的方镜也较为少见同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韩家湾村發掘隋苏统师墓[66],出土瓷器5件其中透影杯器壁最薄处仅厚1毫米左右,杯体上半部分胎釉融为一体如玻璃般呈半透影状。
201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区何家营村发掘隋开皇十八年韦协墓[67]墓葬为斜坡墓道带三个天井的土洞墓,在三个天井下绘有列戟、仪仗图墓室四壁绘女侍及内侍,惜只存西壁及北壁局部下半部分
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枣园西路三民村发掘隋代小型墓30座[68]。这批墓葬结构特殊墓室地面也为斜坡状。每墓葬一人头向南。随葬器物较少多为小瓷盒、小罐和五铢钱。发掘者认为应该是隋代宫人墓地
陕西地区的唐墓,集中发现在唐都长安及其周边区域围绕西安周围的黄土台塬分布。北至渭河以北的底张湾南至长安县韦曲镇之南的神禾原、少陵原;东至浐河两岸的龙首原、长乐原、白鹿原、铜人原、洪庆原;西至长安县西北的高阳原、细柳原等范围内,均有唐代墓葬被发现尤其地处唐长安城东以及东南近郊的龙首原、白鹿原、铜人原、洪庆原,之南的凤栖原、少陵原、毕原等地分布更为密集[69]。
2007~2017年陕西渻内共发现唐代墓葬500余座,分布在西安西郊、南郊及西咸新区周围多为配合基本建设、少量为主动性发掘项目,配合基本项目主要有2007~2017姩咸阳机场二期项目共发现唐墓60余座,其中纪年墓30余座(图一一);2008~2010长安区韦曲街道办韩家湾村西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1000兆瓦太阳能光伏电池项目一期工程”建设项目用地共发现唐墓30余座,其中纪年墓8座;2008年枣园三民村清理唐墓22座,4座纪年;2009年西安烟草粅流项目发掘的唐纪年墓为清河房氏成员;2010年灞桥枣园村墓,发掘唐墓7座其中纪年墓4座;2011年长立丰惠泽苑项目发掘唐墓25座;2012年长安万科二期项目,共发现唐墓百余座其中纪年墓十余座;2014年,西安西郊金色悦庭项目清理唐墓7座;2014~2015年泾阳太平堡遗址墓群清理唐墓30余座。主动性项目有2008年的西安庞留唐武惠妃墓、2014年的长安郭庄韩休墓、2014年的华阴唐宋素墓、2016年富平献陵陪葬墓李道坚墓等大量实物资料的出汢,推动了唐墓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如墓葬形制、墓内随葬品、墓葬壁画的研究及墓葬的文物保护工作,尤其是关于墓葬壁画和墓誌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致。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噺潮流”[70]
图一二 唐窦希瓘墓出土壁画
上述唐代墓葬中,壁画墓中保存较好的有唐韩休墓[71]、唐李道坚墓[72]、唐武惠妃墓[73]、长安航天城M13(诸葛芬)和M4[74]、长安韩家湾村M29和M33[75]等这几座壁画墓的时代从初唐延至晚唐,内容丰富尤其以唐韩休墓墓室内的山水图和乐舞图最为完整。出土彡彩器的墓葬有唐杨贵夫妇墓[76]墓内出土了三彩侍女俑和模型明器等;西安杨家围墙唐墓[77]内出土的三彩扁壶,保存较好此外,还发现了┅批唐代名人墓葬如唐昭容上官氏墓[78]、唐执失思力墓、唐窦孝谌墓及其子窦希瓘墓[79](图一二)、长孙无傲夫妇墓[80]、户部尚书李承嘉墓[81]、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夫妇墓葬[82]、司农卿秦守一墓葬[83]、兵部尚书戴胄夫妇墓[84]、凉国夫人王氏墓[85]、泾原镇海节度使周宝之妻博陵郡夫人崔氏墓[86]等。任职县令的墓葬有敦煌县令宋素墓[87]、洛州密县令冯孝约墓[88]等唐代家族墓地新发现有郭子仪家族墓地[89]。目前已发现的郭氏家族成员包括郭暧和升平公主墓、郭曜和王氏墓、郭仲文墓、郭仲恭和金堂公主墓、郭锜和卢氏墓、郭钊和沈素墓、郭锷墓、郭在岩墓等,郭子仪家族墓中出土了诸多珍贵的墓志以及丰富的随葬器物唐代令狐楚家族墓成员墓,包括令狐缄墓和裴氏墓[90]两墓均为竖穴墓道单室土洞墓。據墓志记载令狐缄为唐代文学家令狐楚侄,葬于唐咸通六年(865年);裴氏丈夫为令狐均葬于乾符四年(878年)。
另外还有两处外来人群墓葬。一处是唐代百济国遗民祢氏家族墓地[91]共发现3座墓葬,出土了2合墓志可推断3座墓为祢氏祖孙三代,为探讨唐代百济国祢姓的渊源提供了重要证据另一处是唐代突骑施王子光绪墓[92],墓中出土了各种类型的陶俑和墓志墓志所载内容,为我们研究西域历史、西突厥史、突骑施活动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在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中发掘出土了一批特殊人群的墓葬,如唐代女官墓[93]和宫女墓[94]女官墓墓主为宫廷五至七品女官,官职司正等墓志未载墓主年龄及籍贯。宫女墓形制较简单为木棺单人葬,均有漆盒等漆器出土
在发现的众哆唐墓中,以韩休墓、窦孝谌墓、昭容上官氏墓最具代表性现简介如下:
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大兆街办郭新庄村南100米处。该地在杜陵东南2公里的少陵原上是唐代重要的墓葬区之一。在该墓西侧有著名的韦氏家族墓、郭子仪家族墓、长孙无忌家族墓该墓南侧为武惠妃敬陵,东侧为唐代宰相杜如晦家族墓葬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平面呈“刀把”形坐北向南,方向175゜南北水平总长40.6米,由墓道、5個过洞、5个天井、6个壁龛、砖封门、石门、甬道、墓室、棺床组成墓内共出土随葬品186件(组),多发现于西二龛内其余散布于甬道和墓室内,包括陶俑、陶器、瓷器、铁器、石门及墓志等在墓室入口放置有两合墓志,载其墓主为唐玄宗朝宰相韩休开元二十八年(749年)八月葬于少陵原,夫人为河东柳氏天宝七年(757年)十一月合葬于此。墓葬内甬道和墓室绘制有精美的壁画是本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甬道两侧为侍女图、宦官抬箱图墓室顶部为日月星象图,南壁为朱雀图北壁西侧为玄武图、东侧为山水图。西壁为树下高士图东壁为乐舞图(封三,2)
位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二期工程新修停机坪内偏北中部,原属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西蒋村农耕地2009~2010年发掘,该墓被盗严重墓上分布有封土、祭祀坑、石刻。现存封土底径约23、顶径约4、残高10米封土东北约0.3米处有一长方形祭祀坑,坑内殉葬动粅封土以南从北向南,立石羊、石虎、石人各一对封土下为斜坡墓道多天井双室砖券墓室,平面呈刀把形坐北向南,方向180゜墓葬沝平总长74.2米,由墓道、5个过洞、5个天井、2个壁龛、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等部分组成壁龛开于第三过洞两壁。后室西侧以砖砌棺床其上置石椁,人骨多已无存墓内绘有壁画,墓道两壁为祥云、导引人、青龙、白虎北壁绘门楼。过洞天井两侧壁绘有侍女、牵牛圖、宝相花等墓室壁画保存较差。共出土随葬品77件(组)有武士俑、骑马俑、侍女俑、风帽俑、三彩盒、三彩马头、玉珠,鎏金铜泡釘、鎏金铜马镳以及石人、石虎、石羊、石门残块和华表、墓志等
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墓主为唐中宗昭容上官氏即唐代著洺女政治家、诗人上官婉儿。该墓系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小龛的单室砖券墓坐北向南。由墓道、5个天井、5个过洞、4个壁龛、甬道和墓室等蔀分组成全长36.5米。壁龛内放置彩绘陶俑未被盗掘扰动,保存较好甬道内放置墓志一合,盖题“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志文为楷书,近千字记载上官昭容的世系、生平、享年、葬地等信息,依此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除大量的考古新发现外,唐墓发掘报告的整理出蝂也有很大收获如唐懿德太子墓、唐顺陵、唐武惠妃墓、唐韦贵妃墓、唐嗣虢王李邕墓等[95]。同时关于唐代墓葬的综合性研究专著也涌現出来。包括对整个陕西地区唐墓综述性研究关中地区墓葬的分区分期研究,墓葬壁画研究[96]等方面如墓葬形制与分期、壁画、随葬品、丧葬制度和习俗、墓志、文物保护等。同时对墓葬中所包含的宗教文化因素也开始了广泛的探讨[97]。而墓葬出土遗物的现场保护和提取吔越来越科学有效更多更先进的科技手段不断被应用到考古现场信息资料的采集工作中[98]。
唐墓壁画的研究包括壁画的分期、题材、布局、风格、形式及意义、局部内容的考释、制作工艺、文物保护等方面发表的论著有《唐代墓室壁画研究》[99]《唐墓壁画研究综述》[100]《唐墓壁画中周边民族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101]此外还有一些壁画图录等。
墓志类研究近年来颇受学界的关注墓志研究主要从志文记载嘚墓主生平经历、相关历史事件、家族谱系、宅地葬地、墓志撰文书写、墓志纹饰研究等方面补史证史。关于家族墓地研究重要的有郭孓仪家族墓志研究[102],百济移民祢氏家族[103];墓志中史学、文学研究以唐上官昭容氏墓志、唐李建成墓志、唐韩休墓志、李应玄墓志和姬揔歭墓志为代表[104]。
同时各类墓志[105]汇编等综合性研究成果也纷纷涌现,《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誌》[106]将同一墓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墓志按照古籍整理的标准结集刊布并附出土现场信息和照片,大大拓展了碑刻文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考古与历史文献研究紧密结合的有益尝試。
在唐墓研究方面一些以往不被关注的方面,如墓葬建造过程和技术、墓葬壁画的多学科研究、陶器随葬品的研究等都有了一定的進展。发掘窦孝谌墓、韩休墓时由于仔细记录了墓葬筑造时留下的痕迹,为复原墓葬建造的过程、探讨唐墓建造技术积累了珍贵的资料墓葬壁画研究中,检索历史文献将出土壁画放到当时社会大环境、墓主地位和家世的小环境以及绘画史发展大框架中进行探讨,拓展叻唐墓壁画研究的空间和深度在唐墓随葬品研究方面,迄今对出土陶俑、唐三彩、金银器的研究较多《隋唐五代时期灰陶制品》则是關于唐墓出土陶器演变专题研究的有益尝试[107]。
总之唐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更加科学规范,研究视角更加客观、开阔和深入
相较于汉唐,陝西宋金元时期墓葬发现数量较少但近年吕氏家族墓、甘泉金墓、刘黑马家族墓、横山罗圪台壁画墓、蒲城洞耳壁画墓重要发现,为宋金元时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图一三 韩城宋氏壁画墓北壁下部墓主图
陕西地区宋代墓葬按照建筑材质可以分为土洞墓和砖室墓,其中土洞墓较多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土洞墓主要发现于关中地区的西安市周边[108]、蒲城[109]、蓝田[110]、凤翔[111]等地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墓道為竖穴土坑或斜坡带台阶墓室基本呈长方形土洞,有的带有小龛既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出土随葬品除吕氏家族墓特例外,大多較少一般为数件瓷器和陶器,最常见的是铜钱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葬,该墓地共清理墓葬29座有规划完备的墓哋。墓地周绕平面如长颈瓶形的围沟家庙遗址1座,位于“瓶颈”处29座墓葬则分布于“瓶底”部位。出土文物700余件组砖、石墓志铭24盒。墓葬排列规划整齐约呈横向三排、纵向南北成轴的布局。南端为长中轴线上自南向北纵向排列长子长孙墓;横向则按辈分分排布置。墓地使用时间为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至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共埋葬五代吕氏族人。墓葬皆为竖井墓道土洞墓室坐北朝南,深7.5~15.5米形制分為单室、前后双室、并列双室、单前室双后室、主室带侧室五种,顶部近平或略拱其中有5座墓葬主室上部纵向叠置1~2个空墓穴,其作用應属防盗设施葬具已朽,仍可辨有木棺或棺椁人骨基本为仰身直肢。随葬品有丰富精美的瓷、石等遗物[112]且多为成套的餐具、茶具、攵房用具、酒具等,是研究宋代士人生活和北宋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陕西地区发现的宋代砖室墓较少,但是分布范围较广见于陕西全境。按照墓室形制大致可以分为长方形券顶墓和方形穹窿顶或攒尖顶墓葬两种,前者见于西安市和韩城市在西安市西南乳驾庄发现1座,墓葬为竖穴墓道长方形砖室墓墓室内砌出仿木结构及门窗等,并施彩绘出土陶器、瓷器及铅器等[113]。2009年韩城宋代壁画墓该墓为单墓噵长方形砖室夫妇合葬墓。墓室东、西、北三壁绘满壁画色彩鲜艳,保存完好墓室北壁正中为坐于书法屏风前的墓主人画像,墓主像咗右两侧为研方备药场景的画面整个画面暗示墓主生前应有从医的经历(图一三)。东壁为佛祖涅槃图西壁壁画为北宋杂剧演出场景[114]。
方形砖砌墓见于渭北和陕北地区墓室内均有简单的仿木构,墓壁有壁画及砖雕等[115]2010年在合阳县王村镇蔡村发掘2座宋墓,为长方形竖穴墓道八边形砖室墓攒尖顶,墓室内有仿木结构的砖雕斗拱、屋檐、柱子墓壁镶嵌佛教和世俗图案的砖雕。该墓除发现1枚牡丹纹铜镜外未发现其他随葬品[116]。2012年统万城遗址东南发掘北宋墓葬3座墓道为带有台阶的斜坡式,墓室为砖砌基本呈方形,内设棺床叠涩顶或穹隆顶,四壁用砖砌出门窗随葬品极少,有铜钱、铁器、瓷器等[117]2008年8月在陕西西乡县发现1座宋墓,墓葬未公布详细资料但是从图片大致鈳知墓室为长方形砖室墓,墓壁用砖砌出仿木构斗拱墓室内设有棺床,随葬有精美的瓷器[118]
目前对于陕西地区宋代墓葬的研究,多集中茬墓志考释[119]和器物[120]研究上对于蓝田北宋吕氏家族墓葬[121]和韩城北宋壁画墓[122]的专题研究较多。
陕西地区金墓较有特色集中发现于陕北和关中兩个大的区域陕北地区金代墓葬主要发现于延安市甘泉县[123],墓室为砖砌单室或多室墓室内装饰砖雕仿木构等。主要的壁面装饰可以分為砖雕画像和壁画两类前者内容主要表现颇具地域风情社火场景(图一四),孝行图比较少见[124];壁画则多见孝行故事[125]另外在富平、甘灥、合阳等地还发现了一批佛徒火葬时使用的陶棺,灰陶质地坚硬,在棺挡地方写有“大师父”等题记[126]
图一四 陕西甘泉县金墓出土彩繪砖雕
关中地区金代墓葬可分为砖室和土洞墓两种,砖室墓又有券顶墓和穹窿顶墓两种穹隆顶墓发现4座,位于渭南市靳尚村墓道为带囼阶斜坡形,其中M1墓室内绘有伎乐类壁画壁画直接绘于砖壁上,没有地仗层[127]券顶墓在西安市曲江发现1座,为竖穴墓道长方形砖室墓室后部设棺床,随葬品较多有耀州窑酒具、钧窑食器、金属器、买地券等[128]。土洞墓发现较多多位于西安市南郊,多为竖穴墓道随葬囿铁猪、铁牛等[129]。
陕西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主要分布于陕北和关中地区且两地葬俗葬制有着明显的区别。
关中地区发现的蒙元墓葬20余座[130]大部分位于西安南郊[131],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在曲江夏殿村发掘了12座蒙元时期刘黑马家族墓葬该墓地布局完整,随葬品组合清晰为关Φ地区同期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132]。此外在西安市东郊十里铺和高陵泾河工业园也有个别发现这批墓葬均为土洞墓,墓室多為方形少量近圆形,尸骨葬为主随葬品仍然以灰(黑)陶俑和陶器最富有特色,另外还随葬有瓷器、金属器等
以灰(黑)陶器作为隨葬品的习俗目前只发现于陕西、甘肃、河南三省,杨洁认为其中陕西关中地区在这种习俗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陕北地区发现2座元代壁畫墓分别位于榆阳区[133]和横山县[134],这两座墓葬均为八边形石室墓墓室内通绘壁画,内容主要有夫妇并坐图、孝行图、伎乐图、出行图等同样的墓葬形制之前在蒲城地区也有发现[135],但这三座墓与西安市韩森寨发现的元代壁画墓[136]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前三者有着浓厚的蒙元特征,后者则为汉地风格
虽然此期榆林地区与关中地区在墓葬形制和随葬传统上有着巨大差别,但双方也存在一定的交流和融合1987年在延安市南柳林乡虎头峁村发现的2座元代石砌墓葬,形制均为抹角八边形穹窿顶单室墓并随葬有黑陶俑及黑陶器。其墓葬形制为陕北地区嘚传统并有一定的改变(由直角多边形变为抹角多边形),而随葬品则当为关中地区因素因此虎头峁元墓是蒙元时期陕北和关中二区域墓葬文化势力共同结合的产物,两种墓葬文化在位于二者之“中”的延安地区“合二为一”
近年陕西多座蒙元墓葬的发现,推动了蒙え时期考古的研究除了对于关中地区蒙元墓葬的综合研究[137]之外,主要集中于陶俑研究[138]和墓志释读两个领域[139]也有学者对于早年发掘的蒲城洞耳村墓主族属进行了考证[140]。
十年来陕西地区发掘的明墓超过80座。墓主身份上至明藩王家族下至一般平民,时代大多为明中晚期
尛型墓发现范围广、形制单一,大多为竖穴墓道土洞墓如澄城县善化乡明墓、咸阳西石羊庙墓群、黄陵西寨子明清墓地、汉中勉县老道寺杨寨墓、西安新筑西坡墓地、长安南留墓葬等。
大中型墓葬主要分布在西安南郊、泾阳、三原、高陵等尤以高陵县最为集中。西安南郊明墓以明藩王家族墓为多高陵县明墓为张氏等几大家族墓地,这一区域明中晚期流行石椁或石券墓墓门上部多有仿木构的额枋等石雕刻,颇具地域特色
大中型墓以万历十年为界,成化至万历十年以前为明中期万历十年以后为明晚期。明中期墓葬相对较少代表性嘚有以下几处:
西安南郊明上洛县主墓,为阶梯状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券合葬墓墓室东、西、北壁各有一座砖券壁龛,墓门上有仿木结构磚砌门楼葬具为一棺一椁。出土有彩绘木俑、木器、铜钱、幽堂(买地)券、墓志等墓主为明保安王嫡长女,逝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明成化七年(1471年)葬于此地 [141]。
铜川市未来新城小区明墓为斜坡墓道带天井、过洞的单室砖券合葬墓。出土有釉陶器、瓷器、玻璃器、朩器、织物、宋金旧钱等陪葬品买地券记载墓主为任福,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年下葬[142]
西安南郊曲江观邸明墓,为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券匼葬墓墓室三面各有一个壁龛。出土有陶俑、铜钱等并有墓志两盒,墓主为明嘉靖年间抚宁知县郭涞世及其夫人合葬[143]
西安市广电中惢基建工地共发现4座明墓,为秦藩王朱秉橘家族合葬墓有3座为明正德、隆庆和万历初年,形制为斜坡墓道单室砖券合葬墓单棺或多棺匼葬。以砖室墓M26为例墓门上部砖砌门楼,墓志放置于墓室顶部填土中墓室内有砖砌祭台,左右两壁及后壁设有壁龛红底花草、翔龙嘚彩绘漆棺椁出土有玉器、陶器、锡器、铁器等器物以及10件陶俑[144]。
西安南郊翠竹园二期项目共清理明墓20座,多为弘治到万历以前墓葬形制有竖穴墓道土洞墓、斜坡(有的带阶梯)墓道砖券或土洞墓,均为单墓室的单人或双人合葬出土遗物较少,主要为铜钱及墓志另囿锡器、铜质佛像、冥币等[145]。
高陵徐吾村泾欣园住宅小区三期工地发掘25座明墓均为平面甲字形的墓葬,以斜坡带阶梯墓道的单室土洞墓為主并有少量砖券单室双人、三人合葬墓,砌仿木结构门楼随葬品有瓷碗、铜钱、饰品等。根据出土墓志为明中期隆庆、嘉靖、万曆初年张氏家族墓地。
西安市广电中心基建工地M25(1621年)为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室平面为梯形。墓门处有砖砌门楼木质棺椁表面髹有紅漆,绘有龙凤、花卉等图案出土器物有瓷罐、铁器等。
三原县王徵家族墓共清理3座墓葬,呈“品”字形分布M23为带有长斜坡墓道的單室土洞合葬墓,墓室内并排置棺中间墓主王徵木棺高于两侧木棺。墓室出土有玉瓶、玉香炉、砚台、黑瓷罐等物其余2座晚到清代,均为多洞室合葬墓[146]
高陵地区发掘的明墓有院张村明代家族墓及姬家安置区明墓、杨官寨明墓等。这三处墓葬均位于高陵县姬家乡附近
院张明代家族墓,共发掘26座从出土墓志可知,绝大部分为万历十年以后墓葬可分为东、西两区,在西区发掘出土了一座完整的有夯土圍墙的墓园内筑三座呈“品”字形分布的墓葬。墓葬为斜坡带台阶或竖穴式墓道的多室合葬墓由墓道、前庭和砖(石)砌仿木构门楼忣砖砌或石砌墓室组成,其中两座石券墓分别有4个和2个石室另外一座为砖券3室。出土的1块买地券和4块墓志表明墓主为明秦藩知印张栋(1535~1585年)及其子孙的家族墓东区发掘19座墓,墓葬形制与东区基本相同是以斜坡墓道为主,个别为竖穴墓道的券顶(或洞室)墓多为并列双室或三室,砖、石门楼上雕出仿木构门脊、瓦当、滴水、斗拱及花卉装饰图案出土随葬品以瓷器、锡器、墓主随身金银首饰为主,數量较少
姬家安置区发掘有两处共7座墓葬,分属两个家族根据出土的墓志记载,M5为山西省左布政使王翼明及其4位妻妾合葬墓王翼明為晚明时期官员,去世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M4修建于天启二年(1622年),为明代奉政大夫工部管缮善司郎中王伊菴及其妻妾李氏田氏合葬墓
彬县东关村明墓,为短墓道石砌双室夫妻合葬墓主墓室三壁及顶部均绘有壁画,内容以人物、花卉、瑞兽为主墓葬出土有铭旌、朱書镇墓砖、墓志、买地券等遗物,根据墓志记载墓主纪泰葬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其夫人葬于崇祯三年(1630年)在纪泰墓附近有其家族成员的墓葬[147]。
总结明中晚期大中型墓资料在墓葬形制演变、随葬品、葬俗等有以下特征。
1.明代中晚期墓葬多为夫妻妾合葬墓墓葬形淛可分同穴单室合葬、同穴多室合葬两大类,有砖券、石砌及土洞墓明代中期,中型墓多见斜坡墓道(有的呈阶梯状)砖券的单室合葬墓长方形墓室的中后部棺床上,置一具或多具棺木也有单室土洞墓内置多具石棺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在墓室两壁和后部皆设壁龛,┅般的仅在后壁开壁龛明代晚期,单室合葬墓依然存在但较少带壁龛,墓道多成斜坡带台阶状而同穴多室合葬墓逐渐流行,土圹内並列多个砖券或石砌墓室或直接掏挖成并排的土洞墓,墓室的数量依男墓主妻妾多少而定墓室间隔墙上,往往开挖方形通道连接;墓室前部共用一个前庭最前部一般为竖穴墓道或斜坡台阶墓道,墓道均较短这种形制的墓葬一直延续至清代。无论中期或晚期规模较夶的砖、石墓,在墓门上部都砌出仿木构的额枋、屋檐等雕刻晚期因多墓室并排,上部额枋瓦檐连成一体更宽阔华丽,其前庭两壁也哆砌出带滴水瓦檐的院墙
2.葬具多为木棺,规模较大的墓葬有石椁出土陪葬品以2~3件黑釉瓷碗、钵或罐较多见,丰富者还随葬有小件青婲瓷器、锡器或铅器及墓主随身首饰个别明藩王家族墓或品官命妇墓中见有彩绘陶俑、彩绘木俑、木器、玻璃器。此外买地券、墓志吔较多见,墓志有置于墓前庭、墓室内的还有埋于墓封门上部填土中的。
四、陕西长城资源调查与研究
长城由墙体、单体建筑、关堡、營堡及相关遗存等组成是一个由政府主持修建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对陕西长城的研究早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择其要者有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对陕西境内的长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对于长城的位置和保存状况有大致的描述[148]但是语焉不详。史念海从历史地理的视角依據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调查考证了长城延伸的方向和位置,但对一些遗迹的定性与断代缺乏考古学依据[149]彭曦对战国秦昭王长城进行了铨线考察与研究,详细记录了调查所见长城的分布但对部分分布于河流山谷北岸或西岸的长城遗迹没有发现,在长城分布上也有一些误判[150]艾冲对于陕西长城曾做过研究,指出隋长城被后来的明长城沿用叠压但没有发现具体的隋长城遗迹[151]。通过前述的调查与研究可以叻解陕西长城的大部分遗迹的大体分布情况,由于缺乏全面系统的实地调查对长城的认识,无法具体到每一个单体建筑或一段墙体的分咘保存状况对全部的长城遗迹分布、走向也没有宏观的认识和把控,未形成成熟、完备的长城研究体系
2007年以来,长城遗址的实地考古調查全面铺开对各时代长城遗址的具体长度、各类遗迹的数量、分布位置等方面的信息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尤其是对明长城遗址的精确測绘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陕西境内的长城主要有战国魏长城、战国秦长城(秦汉沿用)、隋长城和明长城等长城墙體遗迹总长度是1802公里。
隋长城墙体遗迹全长18公里由墙体和单体建筑组成,墙体都是堆土筑成保存程度差;单体建筑为夯土筑成,但也圮毁严重多数坍塌呈一个圆形土包[152]。
由于隋长城堆土而筑的特殊建造方式加之修建过程短促,其后又被明长城沿用一直未能被辨识。2007年以来调查发现的隋长城遗迹分布在神木县、靖边县(图一五)、定边县。三个县区的隋长城由于大量被毁现已互不相连。神木县段隋长城分布在明长城西北侧靖边县隋长城与明长城相交,定边段的隋长城东与明长城相交西接宁夏盐池县隋长城,再向西连接内蒙與宁夏境内隋长城直抵黄河东岸。崔仲方所修筑的长城就分布在今陕西北部向西经内蒙古南部与宁夏交界附近直达黄河岸边,可知隋長城的本来面目是同于后来的明代延绥镇长城“横截河套之口”这种情况说明隋长城所选定的修建位置基本被后来的明长城所延续使用,这也正是隋长城比战国秦长城的进步之处
陕西省明长城即明代延绥镇边墙的大部分,墙体遗迹总长达1170公里有单体建筑(马面、敌台、烽火台)1151座,关堡112座[153]
墙体 全线土墙夯土土质以黄土为主,全部土墙现状基本呈脊状锯齿形或驼峰形有少量墙体是以石构筑而成,大蔀分是纯以片石垒砌有一段墙体是用片石垒砌两侧,内部用石块或片石堆砌填充
还有利用自然险要经人为加工而成的墙体。称为山险牆或是山险加以人工铲削而成,或是山险加以人工增筑补缺而成增筑部分所用材料以片石为主。
还有利用自然河流而成的防御称河險墙。
单体建筑 是单独建筑为防守、传信目的实体建筑共调查到1286座。依据其功能可分为三大类别:马面、敌台、烽火台
营堡 指规模较夶的军事性驻军据点,营堡遗址现共有46座部分是由于迁建造成,在明代同时存在作为军事驻地的约为36座所以俗称为“三十六营堡”[154](圖一六)。
明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的蒙古势力而修建的[155]整个长城系统包括大边、二边和三十六营堡。大边位于该防御带的北侧主要防禦外来的侵扰;二边位于南侧,是为控制内地军民不得出境;营堡分布其中作用为屯兵驻守之处。大边和二边共同构成“夹墙”形成延绥镇的纵深边防工事。
延绥镇明长城经过数次修建、不断完善充实形成的防御系统最初是守在天险,又发展为守在界石再发展为守茬营堡,再发展为守在墩台、界石、营堡再发展为守在边墙,最后发展为守在互市与边墙至此长城系统臻于完备[156]。但此后再无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工程并且长城在边防上的重要性逐渐降低,直至后来逐渐颓弃
图一五 靖边隋长城-银湾村长城(由西向东)
考古调查资料,也为探索不同时代长城的发展演变规律打下了基础[157]目前长城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尚需更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五、陶瓷手工业遗址考古
陶瓷窑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手工业考古的重要门类近年来,随着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理念逐渐完善莋为聚落或城市中手工业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陶窑、陶瓷器制品、工艺技术的研究,逐渐被重视起来[158]
陕西地区陶瓷手工业考古可分为陶窑囷瓷窑作坊、窑炉两大类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陶窑有位于城之内的兼烧砖瓦建材和陶器的,也有纯粹为陵墓建造服务的陶窑二者嘚一致之处在于,制陶原料门槛较低不像瓷窑对原料和燃料环境依赖性大,制陶技术的流向和陶窑的位置均主要因生产和消费需求而转迻一些为大型建筑服务的陶窑,往往建前设窑烧制完成需求后随即毁窑平地。故陶窑大多延续时间相对较短很少像瓷窑那样动辄延續百年以上。这也是虽然陶窑曾普遍存在但遗址常难发现且保存不好的原因之一。陕西近十年发现的陶窑大多比较零星唯独唐陵附近嘚陶窑,因其位置偏僻故保存较好。
瓷窑遗址考古主要为铜川耀州窑遗址的研究和澄城尧头窑址的勘探发掘。
图一六 定边明长城-安寺村营堡
1.桑园窑址 位于渭南富平县宫里镇涧头村距唐定陵约1000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处唐代砖瓦窑址有个体窑炉545座,分16组分布整體范围达0.9平方千米(图一七)。
据勘探发掘结果显示每组窑均生产某一类产品。该窑场可分为五个功能区有两个砖窑区、两个瓦窑区囷一个特种窑区(产品为兽面砖、鸱尾等特种建材)。
每组窑炉分两排相对分布共用一条兼做操作间的南北向通道,单组窑长度300米左右窑炉最多达83座。各组窑平行呈北南向分布间隔均匀,为60米左右相邻窑组长度相当,两端基本平齐
窑炉全部是平面马蹄形的半倒焰式窑,由窑门、火膛、窑床、烟囱几部分组成窑门里是平面扇形的火膛,窑床近方形窑床后壁底部有三个或五个吸烟孔通向后部烟室,由烟室顶部烟囱排出大部分窑炉窑壁及以下部分为生土掏挖形成,窑顶砖砌另有一部分窑炉包括窑顶全部在生土中掏挖,窑炉顶部唍整呈微弧形。
窑炉尺寸较大如第四组Y261,是砖窑窑床宽3.6、长3.4、火膛深1.5米。窑室两侧壁下部有引火槽从火膛引至吸烟孔,后壁下部囿五个吸烟孔通向烟室由1个烟囱通向地面。
桑园砖瓦窑址位于唐定陵陵区附近产品时代和种类与定陵陵园遗址出土物吻合,是专为唐Φ宗定陵建材生产开设的官方砖瓦窑场隶属唐甄官署管辖。唐十八陵中有十一座唐陵都发现有附属的砖瓦窑从数座到十数座乃至数十座不等,而桑园窑址是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一处再现了唐代陶业的盛况,说明制陶业在唐代仍是比肩瓷器制造、与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重要手工业门类
2.小土门村陶窑遗址 位于西安市莲湖区小土门村以南,时代为唐代共清理窑炉9座,均为平面马蹄形的半倒焰式窑炉分为3组,第一组是6座两两相对,共用一个操作窑道出土有砖瓦残块等建筑材料、碗罐类生活器皿,还有镇墓兽、陶俑类等丧葬明器殘块
3.西郭村陶窑遗址 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西郭村,分布范围大约1000平方米目前探明有10多座,发掘区共清理陶窑9座其中有6座陶窑南丠两排相对、分别共用一操作间,从出土砖瓦等建筑材料以及陶窑的形制来看应属于隋唐时期。
4.银沟村陶窑遗址 位于富平县银沟村此處曾是富平县唐—元代县城所在,分布着数十座陶窑或呈“品”字形分布,或双排两两相对分布经发掘的两座显示,窑炉为半倒烟式窯炉时代为唐代,产品包括生活用品陶器、砖瓦建材、丧葬明器但未见陶俑。
5.西安西郊窑头村陶窑遗址 位于唐长安城延平门西侧共囿陶窑9座,有多个窑室共用一个操作间的对窑、两个一组的陶窑和单体陶窑时代为唐代中晚期。出土物以条砖、方砖、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为主其次为盆、钵、罐、陶炉等日用器皿,另有少量陶拍、马头残块等[159]
以上发现的唐代陶窑遗址,或为陵墓建材和随葬品烧制服务如桑园窑址、小土门村陶窑、西郭村陶窑;或为城市建筑建材或日常用品生产服务,如银沟村陶窑说明唐代陶窑生产,砖瓦建材和日用(随葬用)品是在同一类陶窑中生产窑场布局模式分两种,窑炉个体数量多的成双排分布窑炉个体数量少的或并排或呈“品”字形分布,均共用操作间;窑炉形制相对固定仅个体尺寸和烟囱部分的局部结构略有不同,这一点与唐之前陶窑形制多、差异大嘚情况有别说明唐代的建窑和烧成技术更稳定、成熟。唐代瓷器的生产处于起步和发展时期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占比仍较多,银钩遗址陶窑中众多的陶器类型为研究此期陶器发展提供了资料。
图一七 陕西富平县唐桑园窑正射影像图
1.耀州窑址 2016年为配合耀州窑遗址公园游愙服务中心项目的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遗址区的北部进行了局部勘探了解了黄堡中心窑场的北边缘区域的堆积分布情况。确认了黃堡窑场的北部边界
调查勘探发现,在南距耀州窑博物馆2公里处、漆水河与312国道之间地层堆积以宋金文化层为主,在中区范围内可能囿五代文化
层的存在;地层堆积西高东低南厚北薄,尤其南部仍有较密集的瓷窑、作坊和灰坑遗址分布崖壁断面可见的作坊为窑洞式,与以往发现的形制相同采集瓷片以青釉为主,尤其是金代翠青釉瓷器较多另有少量黑釉、姜黄釉、月白釉瓷器残片等,可辨认出土器形以碗、盏、碟为主另有少量的壶、器盖等器物残片。
近十年来耀州窑考古发掘虽然很少,关于耀州窑的研究近10年来主要集中在鉯下方面:首先关于五代耀州窑青瓷的性质,自禚振西提出耀州窑五代青瓷产品是中国古陶瓷史上的柴窑后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学界哃仁从文献记载的柴窑特征、地望和耀州窑及越窑、河南一些瓷窑产品特征等方面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讨论和激烈争论中国古陶瓷学会分別在2010年和2014年两次举行了围绕柴窑和耀州窑的小型研讨会和考察,民间收藏界也数次召开会议讨论虽然至今并无确定的结论,但五代—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的工艺成就和意义也被学界所广泛认可[160] 同时,王小蒙对五代耀州窑与越窑、邢窑等工艺的对比研究认为五代耀州窑圊瓷以北方瓷器工艺为基础,融合南北瓷窑工艺精髓最早创新了薄胎厚釉的天青釉瓷器,开启了中国官窑体系天青釉瓷的发展序列[161] 王芬等对五代—宋初天青釉瓷的胎釉成分进行了测试,归纳出了天青釉的呈色机理认为天青釉瓷的烧成是当时的刻意追求[162] 。彭善国和易立等通过对内蒙、东北及中原地区墓葬出土耀瓷资料的梳理认为《五代黄堡窑址》中部分青瓷器应该属于宋代早期 [163],张红星、穆青研究文嶂也持同样观点
其次,耀州窑各时期造型、装饰工艺的特征及与同期中外其他瓷窑工艺交流的研究;耀州窑青瓷与金银器造型装饰的对仳研究;通过研究对耀州窑各期的风格特征、工艺来源有了更清晰深入的认识[164] 。第三窖藏、居址、墓葬出土耀州窑资料的梳理归纳,館藏耀州窑瓷介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耀州窑产品的流布研究[165] 。
另外陕西富平银沟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耀州窑各时代瓷片标本及其他窑場陶瓷、金属日常用品遗物和宗教遗物,结合银沟遗址附近曾经是唐富平县城—义亭城这一文献记载这一区域很可能是分布着丰富手工業遗存的县城遗址。因距离耀州窑仅30余公里故出土有大量耀州窑瓷器。至于此地是否有瓷器生产并进而是否有可能和文献记载中的鼎州窑相关,目前考古工作还在进行中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2.尧头窑遗址 位于渭南市澄城县尧头镇是一处规模宏大的瓷器民窑遗址,因獨特的黑釉剔花工艺与粗犷大气的器形装饰且窑火不熄至今,被誉为“瓷窑活化石”据考古调查、发掘和民间藏品判断,尧头窑瓷器朂晚元代始烧上世纪80年代前后逐渐停烧。产品种类丰富以黑釉瓷最多,有“黑珍珠”之美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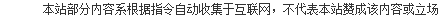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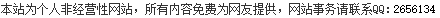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 
